特朗普作为美国总统,权力很大,但并不意味着他可以无限度地为所欲为,他的行动必须在美国宪法和法律框架内进行。最近,他试图对中国征收高额关税的计划,就遭到了美国国内强有力的制约。
2025年8月29日,美国联邦巡回上诉法院以7比4的投票结果裁定,特朗普总统援引《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IEEPA)对多国征收的关税是违法的,因为他缺乏国会的明确授权。法院在裁决书中明确指出,该法案授权总统在紧急情况下颁布某些经济措施,以应对异常和特殊威胁,但并不允许总统采取全面行动征收关税。

这并非特朗普的关税政策首次在法庭上受挫。早在今年5月,美国国际贸易法院就已作出了类似的违法裁决。上诉法院的这次裁定,维持了下级法院的判决。
法院的裁决并未立即生效,而是设定了一个缓冲期,允许关税政策维持至2025年10月14日,以便特朗普政府向美国最高法院提出上诉。
美国宪法第一条明确规定,征收关税、进口税和货物税的权力属于国会,而非总统。特朗普试图通过扩大解释1977年的《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来绕过这一宪法规定。
法院的裁决重申了这一基本原则,指出《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授予总统的是“监管”进口的权力,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将其扩大解释为授权总统通过发布行政命令的方式全面征收关税。法官们在裁决书中写道:“国会似乎不太可能有意授予总统无限征收关税的权力。”
除了司法系统的挑战,特朗普的关税政策还面临来自美国地方政府的强烈反对。

2025年5月,由12个州组成的联盟,包括纽约、俄勒冈、亚利桑那等经济重镇,对特朗普政府提起了诉讼,要求法院裁定其对中国商品加征的关税“违法”,并强制取消2025年以来对中国商品加征的所有额外关税。
这些州在诉状中指控特朗普滥用总统紧急状态权力,频繁援引《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作为加征关税的依据,仅2025年前4个月,他就三次宣布“国家紧急状态”,借此对中国输美商品加征高额关税。他们指出,特朗普的关税措施“未经过任何成本收益分析或公众评议”,甚至部分政策仅通过社交媒体发文宣布,完全绕开国会立法程序。
特朗普的关税政策对美国自身的经济和消费者造成了不小的冲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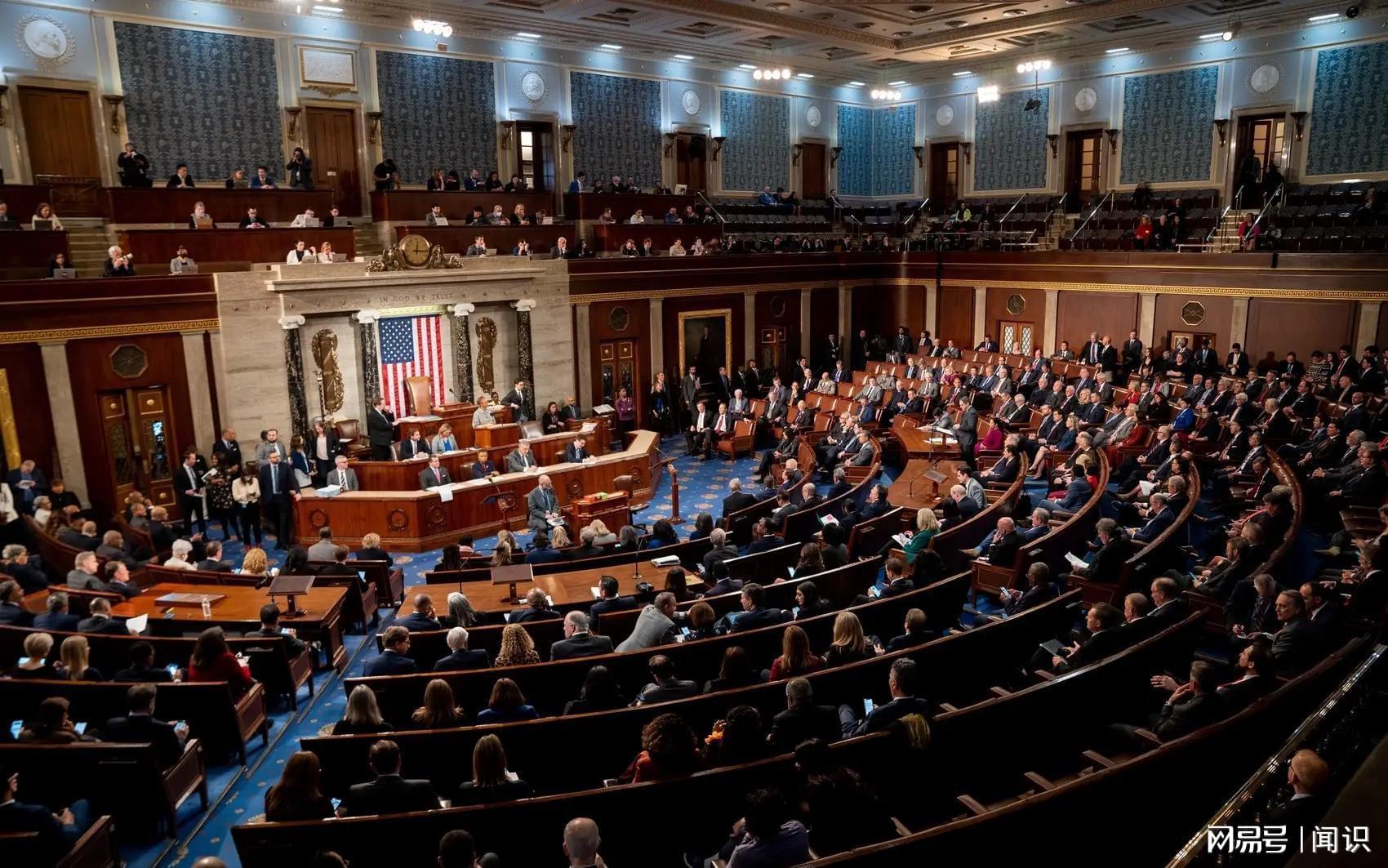
美国企业界怨声载道。据汇丰银行调查,72%的美国中小企业因关税被迫增加成本,77%预计年底前成本还会上涨。大小企业都叫苦不迭,零售商如沃尔玛和梅西百货已公开表示将被迫提高商品售价,经济学家估算普通美国家庭每年将多支出2800美元。
特朗普的票仓农业州也未能幸免。2018年贸易战期间,美国大豆出口就曾暴跌40%,农民被迫低价抛售库存。爱荷华州的豆农们焦虑地表示:“中国买家已经转向巴西,我们的损失永远回不来了。”
加征关税也推高了美国国内物价,加剧了通货膨胀压力。2025年4月特朗普宣布“对等关税”后,美国CPI环比飙升1.8%,创40年最大单月涨幅。
对于联邦巡回上诉法院的裁决,特朗普已誓言上诉至最高法院。他在社交媒体上宣称所有关税仍然有效,并威胁若取消将导致“美国灾难”。
目前美国最高法院9名大法官中,6人由共和党总统任命。法律专家提醒,最高法院近年在“总统权力”案件中并非一边倒。若最高法院最终维持原判,美国政府可能将不得不退还数百亿美元关税。
此案也深陷美国两党政治博弈的漩涡。此次诉讼的12个州中,10个由民主党主政。国会民主党议员普遍支持本次裁决,认为这是对行政越权的必要制约。
在法院裁决的背景下,美国副总统万斯近期关于对华关税的表态也值得玩味。

万斯公开表示,美国对中国商品征收的关税已经高达54%,并明确表示“不会再往上提升”。他强调,现有的关税水平已经“够严重了”,若再提高,只会让美国自己吃亏,依赖中国供应链的美国企业将面临原材料成本上升、产品竞争力下降的压力。
万斯还指出,54%的关税率是在对中国的多轮制裁与贸易安排中逐步形成的,并非空穴来风,是一个独立的、国内评估过的政策阈值。他特别提到,这一数字不会因为中国与俄罗斯之间的贸易关系而再度抬高。
美国法院的裁决和国内的政治压力,可能会对未来的中美经贸关系产生一定影响。
一方面,它动摇了特朗普“极限施压”策略的核心工具,其关税政策的合法性遭到本国司法系统的根本性质疑,政策的稳定性大打折扣。这可能为中美之间的谈判创造不同的氛围。
另一方面,这也显示出美国政治体系内部的制衡机制仍在发挥作用。总统的权力并非没有边界,司法系统和地方政府可以有效制约总统的越权行为。

总而言之,特朗普总统虽然权力很大,但他并不能凌驾于美国宪法和法律之上。他想对中国征收重税的计划,不仅遭到了美国联邦法院“越权”的裁定,还面临着来自美国12个州的联合诉讼以及经济现实带来的压力。
法院的裁决重申了美国征税权属于国会的宪法原则,对总统的权力形成了制约。副总统万斯关于“对华关税不能再高”的表态,也反映了特朗普政府内部对关税政策反噬效应的认识。这场围绕关税的博弈,不仅关系到中美经贸关系,也深刻体现了美国政治体系中的权力制衡与内部矛盾。











